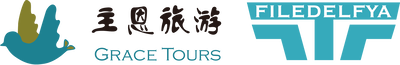2020年4月,我走在中東新冠疫情嚴重的這個國家的街頭,一群十來歲的小孩子,在我們身後,大聲喊:“Corona! Corona!”,就是“冠狀病毒”的意思。我生氣地轉身教訓他們,“我已經在這裡生活幾年了,不是每一個華人都有病毒,希望你們不要用這種眼光來看我們。”從我的土耳其語裡,他們聽出我不是剛來的,就馬上說“對不起,對不起”。類似的情形我們遇見不止一兩次,一些婦女看見我們就立刻戴上口罩;在公車上,人們看見我們的面孔就自動遠離。同工們開玩笑地說:“今天又有人見到我就逃走了。”
其實我已經來到這裡四年了。除了第一年結束之後我回了一次國,算起來已經三年沒有回國了。但回想起2016年3月我剛剛踏上這塊土地的那個深夜,情景歷歷在目:滿街來來往往的都是大鬍子男人、裹著頭巾的女人,還有街邊招牌上如同天書的文字;除了“早安”、“午安”、“謝謝”、“不客氣”之外,我什麼也不會說。
其實我已經來到這裡四年了。除了第一年結束之後我回了一次國,算起來已經三年沒有回國了。但回想起2016年3月我剛剛踏上這塊土地的那個深夜,情景歷歷在目:滿街來來往往的都是大鬍子男人、裹著頭巾的女人,還有街邊招牌上如同天書的文字;除了“早安”、“午安”、“謝謝”、“不客氣”之外,我什麼也不會說。
拿著紙條,勇敢走出去
第一件事就是學語言。當地語言其實比較簡單,只要你會讀字母,就可以拼出單詞和句子。抵達的第二天,我就開始學字母、讀當地語言的聖經了。為了加快速度,我們每星期要背200個單詞。
學會基本發音後,我們就把福音信息寫在紙條上,出門傳福音了。在街上攔住一個青年女性就問:“我可以跟你分享一個好消息嗎?”對方通常會問,“是什麼好消息?”我就拿出紙條給她“讀”福音。拿紙條讀的方式反而讓他們很好奇。我們生澀的發音,她們格外認真聽,甚至有人直接拿著我的紙條自己讀,然後再教我,幫助糾正我的發音。
隨著語言越來越熟練,我們在街頭跟別人可以聊得更多,我們就挑戰自己,今天我要跟10個人傳福音,要跟30個人傳福音,要跟50個人傳福音。“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愛是什麼嗎?”我問。她們開始思考,“是父母的愛嗎?是親情嗎?是愛情嗎?” 我說:“不是,世界上最大的愛是神的愛。”因為當地人基本都是穆斯林,相信阿拉,很多人就會同意:“哦,是的,是神的愛。”然後我們就開始更多分享福音。
如果你看到我們當時的樣子,一定感覺很可笑。為了更專注地學習語言和服事,我第一年特意不用智慧型手機,老款的諾基亞沒有翻譯軟體,我隨身帶著字典和筆記本,表達不清楚的地方就連寫帶畫。不過,即使這樣上帝也能使用,有些人第一次見到我們,覺得我們很可愛,除了認真聽,甚至會留下聯繫方式,發訊息聊天。之後,我們也會請他們吃中國食物、喝茶,再把他們帶到我們的教會。
學會基本發音後,我們就把福音信息寫在紙條上,出門傳福音了。在街上攔住一個青年女性就問:“我可以跟你分享一個好消息嗎?”對方通常會問,“是什麼好消息?”我就拿出紙條給她“讀”福音。拿紙條讀的方式反而讓他們很好奇。我們生澀的發音,她們格外認真聽,甚至有人直接拿著我的紙條自己讀,然後再教我,幫助糾正我的發音。
隨著語言越來越熟練,我們在街頭跟別人可以聊得更多,我們就挑戰自己,今天我要跟10個人傳福音,要跟30個人傳福音,要跟50個人傳福音。“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愛是什麼嗎?”我問。她們開始思考,“是父母的愛嗎?是親情嗎?是愛情嗎?” 我說:“不是,世界上最大的愛是神的愛。”因為當地人基本都是穆斯林,相信阿拉,很多人就會同意:“哦,是的,是神的愛。”然後我們就開始更多分享福音。
如果你看到我們當時的樣子,一定感覺很可笑。為了更專注地學習語言和服事,我第一年特意不用智慧型手機,老款的諾基亞沒有翻譯軟體,我隨身帶著字典和筆記本,表達不清楚的地方就連寫帶畫。不過,即使這樣上帝也能使用,有些人第一次見到我們,覺得我們很可愛,除了認真聽,甚至會留下聯繫方式,發訊息聊天。之後,我們也會請他們吃中國食物、喝茶,再把他們帶到我們的教會。
|
頭三個月,沒有一個新朋友願意來教會。我們幾個同工依然預備等候上帝的工作,堅持每週學習當地語言的讚美詩,預備用當地語言分享福音資訊。第三個月中旬,我們終於迎來了第一位朋友,接著第二位、第三位,更多朋友進來和我們一起敬拜、團契、查經。我們把寫好的個人見證讀給他們聽,然後以小組的形式提問、畫圖。第九個月的時候,有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接受了主耶穌,一直堅守信仰到現在。到了第十個月,我們中間有亞塞拜然人、土耳其人、庫爾德人、摩洛哥人、還有華人,就這樣,我們開始了一個國際教會。
以前在中國大陸,和穆斯林朋友很有距離感,來這裡後發現他們其實很熱情,尤其是遇到需要幫助的外國人。有時我只是向他們問路,他們會直接把我帶到目的地。傳福音,所需要的其實就是放下先入為主的觀念,然後要勇敢。 |
之後我開始學習聖經和神學。當時我身邊大多數基督徒父母其實都不希望子女全時間事奉,在他們眼中,子女有一份體面的工作,然後結婚生子是最好的。媽媽幾次跟我說,希望我全職服侍神,我的回答總是,我沒這麼大的力量,也沒有負擔和感動。
當時我還不太懂什麼,我問上帝:“是你在呼召我嗎?”到了二十歲那年,神學班要結束了,我還在問上帝。但我心裡已經確定,無論神要我往哪兒去,我就往哪去。
那年夏令營講的是“紮根聖經,合一宣教”。營會後,牧者呼召年輕人們參加去藏區短宣。我心想自己肯定不會去,剛畢業我也沒錢,也絕不會跟家人要錢去參加這樣的活動。神卻奇妙地為我預備了所有費用。短短十五天的短宣並沒有讓我弄明白什麼是宣教,不過,在尋找未來方向的時候,那位大哥的一句話就像上帝向我伸出的橄欖枝,於是我就說,“好,我決定去。” 我希望這一年能更深經歷神,明白上帝對我的呼召。
一年以後,我回國不久就聽到從巴基斯坦傳來的消息——一對弟兄姊妹在那裡殉道了。這件事對我來說似乎是上帝的激勵,讓我確信宣教的路是正確的。我心想死就死吧,死亡並不可怕,重要的是死在哪裡。於是幾個月後,我再一次回到中東。
雖然只隔了幾個月,回去之後卻發現社會氛圍有了很大變化。2016年時,當地信仰比較自由,員警知道你在街上講福音,但只要不太過分,他們都不會過問,但現在這種方式已經行不通了。
中東的女孩很值得同情,她們通常結婚很早,有些十五六歲就結婚了。不少男人有暴力傾向,當地離婚率很高,女人不得不獨自撫養孩子。所以年輕女性都不願意結婚,對婚姻和異性沒有安全感,覺得女人更辛苦,要照顧孩子、做家務,還要工作。男人就舒服了,回到家裡就躺著等女人來伺候,連叉子都不自己動手拿,又懶惰又暴躁。很多女人覺得,我可以自己工作養活自己,除非想要孩子才會結婚,但結婚沒幾年又會離婚。
當時我還不太懂什麼,我問上帝:“是你在呼召我嗎?”到了二十歲那年,神學班要結束了,我還在問上帝。但我心裡已經確定,無論神要我往哪兒去,我就往哪去。
那年夏令營講的是“紮根聖經,合一宣教”。營會後,牧者呼召年輕人們參加去藏區短宣。我心想自己肯定不會去,剛畢業我也沒錢,也絕不會跟家人要錢去參加這樣的活動。神卻奇妙地為我預備了所有費用。短短十五天的短宣並沒有讓我弄明白什麼是宣教,不過,在尋找未來方向的時候,那位大哥的一句話就像上帝向我伸出的橄欖枝,於是我就說,“好,我決定去。” 我希望這一年能更深經歷神,明白上帝對我的呼召。
一年以後,我回國不久就聽到從巴基斯坦傳來的消息——一對弟兄姊妹在那裡殉道了。這件事對我來說似乎是上帝的激勵,讓我確信宣教的路是正確的。我心想死就死吧,死亡並不可怕,重要的是死在哪裡。於是幾個月後,我再一次回到中東。
雖然只隔了幾個月,回去之後卻發現社會氛圍有了很大變化。2016年時,當地信仰比較自由,員警知道你在街上講福音,但只要不太過分,他們都不會過問,但現在這種方式已經行不通了。
中東的女孩很值得同情,她們通常結婚很早,有些十五六歲就結婚了。不少男人有暴力傾向,當地離婚率很高,女人不得不獨自撫養孩子。所以年輕女性都不願意結婚,對婚姻和異性沒有安全感,覺得女人更辛苦,要照顧孩子、做家務,還要工作。男人就舒服了,回到家裡就躺著等女人來伺候,連叉子都不自己動手拿,又懶惰又暴躁。很多女人覺得,我可以自己工作養活自己,除非想要孩子才會結婚,但結婚沒幾年又會離婚。
我裡面真實的無力感
這個國家有幾千萬人口,福音率不到萬分之一。有一次我在街上跟一個女孩分享福音,她反過來勸我要做拜功、信阿拉才能去天國。我和她辯論,到最後我很難過,我跟主說,“主啊,她的心如此剛硬,我沒有任何能力改變她,只有你能改變她。”
還有一個朋友,我跟進她一年的時間,把她當作我在這裡最好的朋友。有一次她被燙傷,我們去她家裡探訪她,帶著優克莉莉彈讚美詩給她。她也會參加我們的讀經禱告,與我們分享她在情感上的事,她與男朋友分分合合的十幾次,每次都告訴我。
去年疫情剛開始,我們都居家隔離,我跟她電話,邀請她與我們每天一起在電話裡讀經禱告。她答應得好好的,可是當我再次打電話時,她說:“我是穆斯林,為什麼要跟你一起讀經禱告?”從那之後,我再給她發訊息、打電話,她都不回我,直到我離開,我們都沒有恢復聯絡。我真地希望她可以認識真神。
我能感受到這裡是福音的“硬土”。有一個朋友是很虔誠的穆斯林,也很愛我們,每次來看我們都要走四十多分鐘,而且每次都會帶食物或裝在瓶瓶罐罐裡的零食給我們。哪怕我們不在,她也會把食物掛在門上。有時正跟我們聊著天,突然就說時間到了,她要做穆斯林的拜功了,然後還會給我們示範怎麼做。
有一位媽媽有兩個女兒,都是包頭巾、做拜功的,但她的女兒不太乖。這位媽媽聽我的見證時就說,她很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像我一樣,但是不要選擇我的信仰。她能感受到我的信仰是真實的,但是她還是選擇信她的神。
還有一個朋友,我跟進她一年的時間,把她當作我在這裡最好的朋友。有一次她被燙傷,我們去她家裡探訪她,帶著優克莉莉彈讚美詩給她。她也會參加我們的讀經禱告,與我們分享她在情感上的事,她與男朋友分分合合的十幾次,每次都告訴我。
去年疫情剛開始,我們都居家隔離,我跟她電話,邀請她與我們每天一起在電話裡讀經禱告。她答應得好好的,可是當我再次打電話時,她說:“我是穆斯林,為什麼要跟你一起讀經禱告?”從那之後,我再給她發訊息、打電話,她都不回我,直到我離開,我們都沒有恢復聯絡。我真地希望她可以認識真神。
我能感受到這裡是福音的“硬土”。有一個朋友是很虔誠的穆斯林,也很愛我們,每次來看我們都要走四十多分鐘,而且每次都會帶食物或裝在瓶瓶罐罐裡的零食給我們。哪怕我們不在,她也會把食物掛在門上。有時正跟我們聊著天,突然就說時間到了,她要做穆斯林的拜功了,然後還會給我們示範怎麼做。
有一位媽媽有兩個女兒,都是包頭巾、做拜功的,但她的女兒不太乖。這位媽媽聽我的見證時就說,她很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像我一樣,但是不要選擇我的信仰。她能感受到我的信仰是真實的,但是她還是選擇信她的神。
|
類似的情況太多了,當我越多瞭解越會覺得很多人都不可愛,真的不可愛,靠自己根本就沒有力量去愛他們。我們能做的非常有限,就是真實地活在他們面前,真實分享自己的信仰和見證,但是他們無法接受我們的信仰。面對如此廣大、堅硬的禾場,我常常有一種無力感。
有時我會想,宣教應該讓基督徒中的精英來做,讓那些受過神學裝備、牧養經驗豐富的人來做。將一個人的靈魂帶到上帝面前是一項大工程,神卻呼召了我們這樣的“平民”宣教士。我們在這裡的服事很日常、很淺白:邀請朋友們一起學習聖經,為他們祝福,去家裡探訪,為他們唱讚美詩;最重要是,在他們中間生活。當他們看到我們生活很規律,每天親近主,就知道我們跟其他年輕人不一樣,願意跟我們成為朋友。 |
我們中間有個弟兄,語言說得不太好,但是很會做菜。每次他都很認真、很有愛心為朋友們準備飯菜,跟人交流的時候也是各種肢體語言,但那些本地朋友都很喜歡他,因為看到他身上的真誠。
這裡的年輕人似乎有一些變化。頭一兩年認識的年輕人會直接說自己是穆斯林,但現在有些人會說——我不是穆斯林,或者我是一個掛名的穆斯林,或者說自己是不可知論者。我不知道這個國家的信仰狀況未來如何演變,但我相信神在動工,因為這塊土地是祂創造的,這裡的人也是祂所愛的,祂掌管一切。我所能做的,就是抓住任何出現的福音機會,和人分享福音。因為我知道,很可能我跟這個人見一次面就永遠不會再見了,她可能只有這一次機會聽到福音。
這裡的年輕人似乎有一些變化。頭一兩年認識的年輕人會直接說自己是穆斯林,但現在有些人會說——我不是穆斯林,或者我是一個掛名的穆斯林,或者說自己是不可知論者。我不知道這個國家的信仰狀況未來如何演變,但我相信神在動工,因為這塊土地是祂創造的,這裡的人也是祂所愛的,祂掌管一切。我所能做的,就是抓住任何出現的福音機會,和人分享福音。因為我知道,很可能我跟這個人見一次面就永遠不會再見了,她可能只有這一次機會聽到福音。
我如何能忘記你?
去年爆發的新冠疫情給傳福音帶來很大阻礙,我們的事工停了兩個半月。六月份的時候我們決定不能再停。重啟事工後,第一次出門時心裡還是會擔心,但神跟我說:“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,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;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,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”這給我很大鼓勵,外界雖然動盪不安,但我的心裡有神的平安。
第五次定的航班預計在2021年3月啟程。因為2月14日我要講臺分享,我花了一個星期問神要對我說什麼。神帶領我去思想摩西的故事,摩西四十歲時從埃及逃到曠野,四十年後,神又呼召他回到埃及,但神不是讓他回去重溫以前的生活,而是去將耶和華的軍隊帶出來!我很清晰地領受到神讓我回去的使命,不是我要回去做什麼,而是神要將祂的軍隊從中國帶出來,耶和華的百姓要去到地的四極為祂做見證!
那一刻,我突然覺得什麼都不重要了,對家人和男友的思念都沒關係,如果回不去就再等等吧。沒想到,兩天後,2月16日晚中國大使館發了聲明,2月22日以後的轉機航班,大使館都不會給綠碼放行。我知道剛好有一趟2月19日轉機經歐洲一個國家回中國的航班,當即決定再次改簽。我不確定能否成功,只是將行程交托給主。
2月17日的淩晨五點,我收到改期成功的信息,因為是19日早上八點的航班,我只有一天的時間做核酸檢測、交接工作、跟朋友告別和整理行李。神在祂藉著摩西的故事帶給我的感動之中,打發我回國了。我沒有告訴國內的任何人改簽航班的事,等我終於落地中國,開始隔離,我才告訴他們我已經回來了!
那一刻,我突然覺得什麼都不重要了,對家人和男友的思念都沒關係,如果回不去就再等等吧。沒想到,兩天後,2月16日晚中國大使館發了聲明,2月22日以後的轉機航班,大使館都不會給綠碼放行。我知道剛好有一趟2月19日轉機經歐洲一個國家回中國的航班,當即決定再次改簽。我不確定能否成功,只是將行程交托給主。
2月17日的淩晨五點,我收到改期成功的信息,因為是19日早上八點的航班,我只有一天的時間做核酸檢測、交接工作、跟朋友告別和整理行李。神在祂藉著摩西的故事帶給我的感動之中,打發我回國了。我沒有告訴國內的任何人改簽航班的事,等我終於落地中國,開始隔離,我才告訴他們我已經回來了!
21天的隔離,像是神為了這幾年服侍給我的假期。雖然我整天待在隔離飯店裡,但一想到同工們還在前線堅持,仍然有一群人在福音未得之地為主奔跑,我就覺得很感動,很被激勵。
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對自己的未來方向還不明確,雖然可能已經畢業進入職場,也陸續進入婚姻,看起來挺正常挺正確,但很多人可能並沒有抓住人生的重點,也不知自己該為何而活。以前有國內的肢體問我,“你們在那裡辛苦嗎?你們過得怎麼樣?”現在我回來了,但前線同工們的堅守,讓我更有力量和熱情想要動員更多青年人:我們是耶和華的軍隊,當為主勇敢傳揚福音。
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對自己的未來方向還不明確,雖然可能已經畢業進入職場,也陸續進入婚姻,看起來挺正常挺正確,但很多人可能並沒有抓住人生的重點,也不知自己該為何而活。以前有國內的肢體問我,“你們在那裡辛苦嗎?你們過得怎麼樣?”現在我回來了,但前線同工們的堅守,讓我更有力量和熱情想要動員更多青年人:我們是耶和華的軍隊,當為主勇敢傳揚福音。
離開中東的那個清晨,這幾年陪伴我的兩位大哥大姐一直站在安檢口目送我。他們的眼裡有不舍,也有期待。我不敢回頭,也不敢哭,只能仰著天拼命忍住眼淚。大哥在前一晚的歡送會上說:一個為中東擺上四年青春的青年人,我不相信她的心會忘記這裡。是啊,我的心如何能忘記這塊土地和上面的人呢?在途中轉機時,我打開聖經,正好讀到:“耶路撒冷啊,我若忘記你,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。”
中東啊,我如何能忘記你?我若忘記你,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。
中東啊,我如何能忘記你?我若忘記你,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。